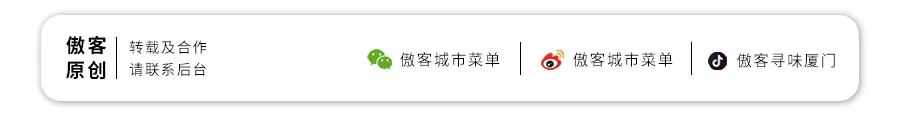(这是2016年刚开始流浪那会,我在贴吧写的记录贴)
以前在昆明流浪的时候,我曾在西山区大观河附近碰到过一个女性流浪者,只不过她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了一副小伙子的模样。
那时正值深秋,已有红嘴鸥陆续从西伯利亚飞往昆明,此地虽号称春城,但温差较大,早晚比较凉快,中午还有些许炎热,一天下来仿佛经历了春夏秋三个季节。
那一阵子,我每天清晨都要背着一个硕大的蛇皮口袋,步行前往位于五华区西昌路的废品收购站,口袋里面则塞满了塑料瓶子和纸皮。
近一个星期的清晨,我路过大观河旁边的人行道时,几乎每次都能看到那个小伙子在同一个地方,躺在同一张木椅上睡觉。
有时中午我赶回藏身处拿食材做饭吃,在路过大观河的时候,发现他依旧还是躺在那个相同的位置上。
我发现他的身躯很单薄,整体衣着还算干净整洁,脑袋侧面枕着个和身材不符的大号登山包,双手环抱在胸前,躯干像虾米一样蜷缩成一团,看起来是一副饥寒交迫的模样。
或许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我感到一阵心酸,忽然觉得对方比我还要可怜,于是便决定做点什么。
于是在卖完废品后,我便跑到篆新农贸市场买了几个肉包子,又向老板讨了个塑料袋,将双肩包里的几个苹果和橙子放了进去。
这些水果也是昨天晚上我在农贸市场收市后及时捡来的,清洗过后便把它们放在背包里,饿的时候就掏出来啃一个。
等我返回大观河岸边的木椅上时,那个小伙子的身躯从右侧卧变成了左侧卧,却依旧还保持着一副蜷缩的模样。
我径直走过去,把食物放在他身前的地上,又想到会不会被路人或环卫工给拾走,于是在犹豫了几秒钟后,便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想提醒他把食物收好。
小伙子被我拍醒的时候脑子还有点懵,随后有点不情愿的从木椅上坐起来,一脸疑惑的看着凭空出现在他面前的我。
我指了指放在地上的食物说,这些东西是我买给你吃的,你把它收好了。
对方没和我搭话,眼睛却已经注意到了身前的食物,而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转过身刚要走的时候,背后却传来了一声清脆悦耳的道谢声。
是女人的声音,悦耳得像是一阵清风拂过后,银铃间相互碰撞发出来的清脆质感。
我内心一震,以为旁边还有人在说话,可当我再次转过身来的时候,身前却只有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发现别人的身影。
见我没反应,对方又重复了一遍道谢,我傻傻的回了句不客气后,这才确定声音的主人确实来自眼前这个小伙子。
我又认真打量了一下对方的外表,虽然身上穿着宽松的男装,发型被刻意剪短成男性化的模样,皮肤也晒得黝黑。
但五官小巧的脸上依然能够看出女性特有的柔和线条,脖颈上没有喉结,如果观察不细致的话,下意识便会觉得对方是个长相有些清秀的小伙子。
但加上刚才的声音来判断,我确信她就是一名乔装打扮成男人模样的小姑娘无疑。
对方被我盯得有些不好意思,惊讶之余,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只能向她挤出一个笑脸,说了声保重后,转身便朝着省图书馆的方向走去。
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假小子,或许她担心识破她真实性别后的我会对她有非分之想。
又或许因为我这个陌生人一点微不足道的善意,让她鼓起了好好生活的勇气。
而她最终是选择了回家还是选择了去找工作,这些我都不知道,不过她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保护好自己肯定没问题。
一旦在街上发现有女性流浪者,帽子叔叔和救助站管理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把她们带走。
要么通过救助站买车票遣返回原籍,要么帮忙安排工作,要么就一直待在救助站里,等联系上亲人后过来认领。
如果不管不顾,任由她们流落街头,那是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的存在。
而至于男性流浪汉,只要你不做出诸如乞讨卖艺,公共场合裸奔之类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不影响到别人,帽子叔叔看到都懒得管你。
如果碰到诸如搞文明城市,或是当地有其他重要活动,那么这些影响“市容市貌”的群体要么通过救助站遣回原籍,要么被送到另一个地方去。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男性流浪汉就比女性流浪者安全,你要知道,兽性一旦占据了人性的时候,有些人是不会在意你性别的。
当你真正跌落谷底,沦为社会中最底层的存在,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成为问题的那一刻,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受到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
刚开始流浪那会,我因为没什么经验,一个人傻傻的跑到公园里面睡觉,结果某次闭上眼后迷迷糊糊的就要睡着时,却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脸。
我顿时睡意全无,睁眼朝手的主人猛瞪回去时,那人却一转身,迈起小碎步怪笑着溜走了,我纳闷的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闭目养神半晌后,凉亭里走进来一个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
我见他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于是便放松了戒心,没成想那家伙和我套了会近乎后,直接开门见山的告诉我这是个同志公园。
对方以金钱为诱饵,邀请我和他唱一出后庭花的戏,把我吓得直接拎包跑路了。
那以后我便不再睡公园,而是选择了拆迁房这种密闭空间,对于流浪汉而言,有时人越少越隐蔽的地方反而越安全。
这种开门见山的坦荡人士我倒不怕,而那种诡计多端,打着关心帮助旗号实则趁人之危欲行不轨之事的家伙就比较隐蔽了。
我在某个广场搭帐篷露营的时候,曾遇到过一个聊得十分投机的哥们,对方在我放下戒心后热情的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还提出要帮我找工作云云。
我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心人,结果晚上洗漱完毕躺床上休息时,对方忽然进入房间,提出要亲吻我弟?
犹如晴天霹雳,我直接从床上跃起,呈现出一副金刚怒目暴跳如雷状,在唬住对方的同时,麻利的收拾东西赶紧跑路。
所以你看,连一个人高马大的流浪汉都难免会遇到同性骚扰,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流浪者,要面对的可是一大群潜在的性压抑群体。
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人性的恶,女性流浪犹如一只肥羊在狼群面前晃来晃去,其风险自然不言而喻。
所以帽子叔叔和救助站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发现女性流浪者后把她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这是最好的保护,也是你很少在大城市里看到流浪女的缘故。
说完女性流浪者,那接下来就说说男性流浪汉的生活吧。
在昆明流浪那会,我所藏身的地方位于西山区大观楼景区附近的大观楼村,那里有好几栋被征收的拆迁房,而我选择了其中最隐蔽的一栋。
这些拆迁房年代久远,里面的家具早已被拾荒者席卷一空,连窗户上面的混凝土钢筋和防盗窗都被撬走了,一眼望去,屋子里只剩下空空荡荡的贫瘠。
一开始我选择睡二楼,某天深夜,我在迷迷糊糊间被一阵手电筒的光线给晃醒,于是便下意识的摸出了藏在枕下的菜刀。
我感到十分乏力,因为刚醒来时身体机能尚未恢复,但手中那个泛着寒光的家伙在给我壮胆的同时,也吓破了对方的胆。
还没等我看清他的脸,他便急匆匆的转过身落荒而逃了。
说来这把菜刀也是我从小区的宝箱里面淘出来的,本就打算留着防身用,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第二天中午,我外出一趟再返回藏身处后,却发现堆放在床上的书籍不见了,其余不值钱的物品也被翻的乱七八糟,也不知道是不是昨晚那个深夜造访的家伙干的。
那天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床架和床垫从二楼拖到了六楼顶层的小房间里。
之所以选择顶层,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一般拾荒者或社会闲散人员在连续爬了三四层楼后却一无所获,就会在边际递减效应的作用下降低期望,不会再有继续往上爬的动力,所以很少有人能发现我。
住顶层的好处是足够开阔且隐蔽,整个天台都是我的小天地。
而坏处也很明显,由于周围没有楼层的遮挡,且小房间的门窗早已被拾荒者撬走的缘故,平时下小雨和中雨的时候还好。
而一旦遇到下大雨,就会有雨水顺着窗口飘进来,连天台上面的部分积水也会顺着地势流进我所藏身的小房间。
小房间的前身应该是个杂物间,没设置地漏,于是我就只好用捡来的撮箕,一下又一下的把雨水从房间里沿着窗户外舀出去。
门窗被撬走后自然也会有风吹进来,不过不要紧,我还在床上加了一个某品牌四季帐篷,天气热的时候我便只搭内帐,它的结构和蚊帐差不多,有效的杜绝了蚊虫叮咬。
天气冷的时候我便再加上外帐,这样不仅防寒还防风,保暖性能非常良好。
总的来说,除了遇到连续几天下大雨,被迫在小房间里“游泳”的情况下住得不太舒服之外,其余时间我都住得很舒心。
在我藏身处不到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条大观河,它属于滇池的主要补给河流之一,在那附近有石阶方便落脚。
白天会有钓鱼佬出没,于是我便在晚上到那里洗衣服,有时也顺带洗个澡。
当然,天气冷的时候我便不在河里洗,而是跑到距藏身处差不多一公里距离的920医院住院部洗。
进入住院部后,随机按一个电梯楼层,挑一间没有病号的房间,就可以在卫生间里痛痛快快的洗个热水澡了。
在大观河附近,距离大观楼正门两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个无人值守的警务亭,那里有个供游客使用的自来水龙头。
而至于大观楼景区,我只进去过一次,印象中收了我五十块门票,但却没有看到预想中的风景,现在想想都有点血亏。
我每天会拎两个1.5升的矿泉水瓶到警务亭那里接水,留着煮饭洗菜用。
我做饭的地方,是一片距离藏身处不到八百米远的树林,那片树林连着滇池,树林中间则有一条汇入滇池的河流。
河流的南面与大观楼有着一墙之隔,一抬头便能看到大观游乐场里面呼啸而过的过山车和慢悠悠转个不停的摩天轮。
和隔壁大观楼景区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比起来,这片鲜有人踏入林子反倒显得有些幽静。
也因为路径偏僻的缘故,平时除了本地的钓鱼佬和带孩子踏青的家长会来这个地方,鲜少会有外地游客造访。
过了桥后,顺着北面的小道一直往前走,就能通往一个颇具规模的西南建材市场。
而在通往建材市场的小道上,还有另一条岔路,沿着那条岔路往前走,便能来到另一个更开阔的地方,这里坐落着几间废弃的活动板房。
早在我发现这些活动房之前,就已经有其他流浪汉住在这里了。
其中一位是三十多岁的景洪老哥,他昼伏夜出,身材肥胖,我几乎每次过来煮饭的时候,隔着板房都能听到他如雷的鼾声。
到了晚上的时候就看不到他的踪影,也不知上哪鬼混去了,我从没看到过他捡废品,而他藏身的地方却从不缺粮油之类的食物。
某次我以肠子快要生锈了的玩笑话为由,用一袋水果和他换了一瓶香油。
而另一间房则上了锁,房间的主人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头子,我有幸参观过那个房间,一进屋便有一股浓郁的药材气息扑面而来。
只见房间的地上码着一堆不知名的中药材,这些玩意全是老头子从山上采来的,白天在外面晾晒,晚上则是由景洪老哥帮他收回到房间里,而他则以烟酒报答对方。
房间里面有床铺,但我却从未看见过他在那里休息,这么浓郁的味道,想必在里面睡觉也不舒服,平时用来午休还行。
和老头子熟络后,他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他的身子骨十分硬朗,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却窜得飞快,在后面蹬着一辆共享单车的我怎么都追不上他。
印象中,老头子家位于西山区某个街道内的回迁小区,房间因为他儿子的功劳,被装修得十分漂亮。
老头子待人接物很厚道,时不时便给我送点吃的,还说要带我去山上找药材,但直到后来我离开昆明时也没再和他碰过面。
我挑选了景洪老哥边上的活动房当做厨房,又从周围捡了几块红砖后,一个简易的灶头便被我码起来了。
而至于火源,那更是就地取材,我在树林里收集了一大堆柴火,把它们码放在活动房的角落里,即使遇到下雨,也能够持续使用个把月。
每天临近黄昏时,在翠湖公园吃够了面包的海鸥便会陆续飞回滇池睡觉,而我则会拎起一只在头天晚上清洗干净的蛇皮口袋,动身前往位于五华区新闻路的篆新农贸市场。
该市场规模庞大,据说所有摊位和商铺加起来有近千个,是我人生中去过最大的菜市场,而在里面,我可以捡到各式各样种类繁多的瓜果蔬菜。
它们当中有不少是“不小心”滚落在地上后摊主忘了捡起来的,还有的是卖相不好的次品,在傍晚收市后还卖不完的话,便会被丢在地上。
当然,我必须掐着时间赶到,否则大部分品相好的蔬果就会被别人给捡走,剩下的大多都是一些品相不好的残次品。
若是去得再晚,那就会被清洁工全扫走,连毛都捡不到。
每次到菜市场捡菜,我一般就捡个够吃两天的量,多的我也不捡,因为捡多了吃不完会放坏掉,这也是一种浪费。
而一旦你贪多捡多,那后面来的人便捡不到好蔬果,那时大家为了早捡多捡就会争分夺秒的把握时机,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内卷。
至于捡菜的人,除了像我这样没有经济收入的流浪汉,还有些属于老弱病残,基本都是社会的边缘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篆新菜市场里面有家专卖破酥包的包子店,口感特别好,而且最重要是,它价格很便宜,1.5元/2个包子。
有豆沙包香菇包,酸菜包和鲜肉包,有时候我懒得跑回去做午饭,就花上个六块钱买八个包子,午饭问题就解决了。
捡完菜后时间尚早,我便会顺着大观河往下走,来到某个有落脚点的石阶上,把里面的瓜果蔬菜倒腾出来清洗一遍。
再用警务亭旁边的水龙头冲洗一遍后,就可以找个安静的角落,掏出一把在菜市场里两块钱买来的不锈钢小刀,削两个苹果或橙子充充饥。
到了晚上七点半左右,此时正是饭店用餐高峰期,也是我的觅食时刻。
于是我便把口袋里的蔬果在某个树丛里藏好,动身前往那几个经常造访的饭店。
来到饭店门口后,我并不会直接冲进去,而是候在外面透过门窗观察一阵子。
等到有客人吃得差不多了,起身买单离开饭店时,我便赶在服务员撤桌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去,手法老练的从双肩包里掏出饭盒,把里面的肉菜一股脑往里面倒。
运气好的时候,会遇到那种应酬的饭局,很多菜都是只动过几筷子的,最终都被我拿去祭了五脏庙。
不过我在打包完饭菜后,也会顺带帮人家收拾一下桌面上餐具,在减轻了服务员工作量的同时,也容易获得别人好感。
当时经常在近华浦路造访一家清真牛菜馆,一来二去跟里面的工作人员混脸熟了,某个服务员甚至说以后撤桌的时候会把菜单独留给我,但因为太熟的缘故,我反而没好意思再去。
刚开始吃百家饭时,我都礼貌的问服务员可不可以把饭菜打包回去喂猫喂狗,用这种话术大部分人都会同意。
当然,也并不是每家店都这么好说话的,去的饭店多了以后,偶尔也会遇到不同意的,服务员会解释说老板不允许这种要饭的行为出现,于是我便识趣的没再出现。
后来我学聪明了,别人不问的时候我就不说,对方反倒还以为我是之前来用餐的客人,见我饭盒装不下,甚至还会拿打包盒过来帮我装多余的饭菜。
觅食完毕,解决完晚饭问题后,便来到了寻宝时间。
我回到藏身处,戴上鸭舌帽和口罩,拎起一只专门用来捡废品的超大号蛇皮口袋。
动身前往位于二环西路的碧鸡名城等高档小区里面打宝箱(翻垃圾桶)。
碧鸡名城属于开放式的高档小区,小区出入口都没有门禁,只有住宅入口才设置了门禁和保安。
于是乎,里面的宝箱就吸引了我这类以拾荒为生的流浪汉。
在白天,宝箱的开发权属于小区里的保洁员,而到了晚上,就属于流浪汉和拾荒者了。
之所以将垃圾桶称呼为宝箱,是因为在里面真的能开出不少对于流浪汉而言弥足珍贵的资源。
如未开封的食品药品衣物,以及各种能拿去卖钱的战损版电子产品,有时甚至能从里面的衣物中翻出软妹币和首饰。
当然,也可以翻出最普通最常见的瓶子和纸皮,这些都是可以拿去卖钱的,是流浪汉和拾荒者赖以生存的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越高档的小区,好装备的爆率越高,当然前提得是出入口处没设置门禁的开放式小区,不然你就只能在保安的眼皮子底下溜进去了。
废品回收主要是瓶子铝罐纸皮这一类,我记得铜的价格最贵,那时高达35元/斤,不过它几乎很难通过宝箱爆出来,反而是在废弃工地/工厂和拆迁房中爆率更高一些。
以至于回归正常生活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抗拒吃甜食,因为曾有过一段吃面包吃到想吐的经历。
我对打宝箱这件事也没什么上进心,经常在捡够能卖出十来块钱数量的废品后就打道回藏身处,放下口袋,拿起地笼,朝滇池树林的方向走去。
这个地笼也是我之前在树林里捡到的,当时它被划破了,被我捡回来用鱼线修补一番后,又勉强可以使用了。
来到滇池树林边,此时一墙之隔的大观楼游乐场已由白日的喧嚣回归了夜晚的宁静,滇池周遭也一片寂寥,只有湖面上漂浮着的几个荧光鱼漂在暗示着钓鱼佬的存在。
我将背包里的饭盒掏出来,把剩余的食物残渣全丢进地笼里,像往常一样,在那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隐秘角落中栓好绳子后,将地笼浸入了湖面。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明天中午我就能收获一顿丰盛的鱼虾。
此时离休息时间尚早,我便会到有灯的地方看看书,我的双肩包里会随身带着一本书,有时是从某个寺庙里请来的经书。
有时是我从地摊上花几块钱买来的旧书,对我而言,什么类型的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打发时间就好。
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我便返回位于大观楼村的藏身处,躺在小屋子里一觉睡到天明。
睡醒后,用提前接好的自来水刷牙洗漱,吃头天晚上捡来的面包,把之前在菜市场中捡来的水果放进双肩包里,留着白天吃。
最后出门,将装有废品的蛇皮口袋甩到后背上,背着它朝五华区的西昌路的某个废品收购站出发。
此时我要经过一个大型停车场,920医院和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些地方都是我捡瓶子的重要地点。
运气够好的话,我便能在抵达西昌路的废品收购站之前,搜集到差不多能卖出20元软妹币的废品。
抵达收购站卖完废品后,时间差不多来到了九点钟左右,这时我会走上两公里,前往翠湖公园附近的省图书馆。
由于来访者不能背着包进入图书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门口负责背包存放的是一个脾气很臭的更年期阿姨。
而她本人似乎并不知道这回事,依旧狐假虎威的仗着手上那么点权力最大限度的为难来访者。
对我而言,到图书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接免费的矿泉水喝,我当时准备了一个2L容量的大号太空杯,天不热的时候,接一次就够喝一整天。
我当时把手机丢了,于是图书馆就成了我接触外界信息的主要媒介,而位于三层的电子阅览室,每人每天可以免费上网四小时。
在这个早就以电子支付为主流,而我却习惯了没有手机的日子,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有时因为没有零钱找给我,于是就把钱记到了下一次。
二层是图书阅览室,有时看电脑屏幕看得眼睛累了,我便到阅览室看看书,或趴在桌上小憩一会。
在图书馆待到十点半左右,我会到翠湖公园里面转一圈,此时冬天还未来,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却早已抵达了春城。
热情好客的昆明人,用手里的面包招待着这群横跨了大半个亚洲,不远万里飞来春城过冬的可爱小家伙。
小家伙们吃得高兴了,便会成群结队的飞到翠湖上空来回盘旋,犹如在跳一支欢乐的舞蹈。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在场的人们纷纷掏出手机和相机来拍照,而小家伙们口中也咿咿呀呀回应着人类的热情款待。
看够了海鸥,我便沿着来时的路,顺着大观河的流向一直走向藏身处。
来到藏身处后,拿起昨晚在菜市场里捡来的食材,拎起两瓶提前接好的自来水,朝着滇池树林的方向走去。
抵达活动房后,我放下身上的东西,来到昨晚下地笼的那个隐秘角落,将它从湖里拎了出来。
有时候运气好,我一晚上便能收获二三十尾小鱼小虾,而有时运气不好,放了一晚上也只有五六尾鱼虾。
我想,捕获鱼虾的多寡,应该取决于当晚诱饵对它们的诱惑程度有多深。
取完地笼,解剖鱼虾,回活动房,淘米洗菜,生火做饭。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完成。
由于条件有限,我一般都会多放点水,将米煮成稀饭,当铁锅内米汤开始沸腾的时候,便放入鱼虾,蔬菜,搅拌均匀。
再煮个十分钟,倒入油盐调料,一锅香味四溢的“柴火河鲜蔬菜粥”就出炉了。
用餐完毕后,返回滇池边洗干净炊具,再用瓶子里剩余的自来水冲洗一遍,用袋子包装好,把它们藏在树林里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中。
接下来,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我又动身前往翠湖公园,看海鸥,看过往的人群,走累了就返回图书馆看书,一直到五点钟闭馆为止。
于是,我又开始重复前一天的日常:到菜市场捡蔬果,到饭店吃百家饭,到高档小区打宝箱,到面包店蹲点,到滇池树林下地笼。
当然,在昆明流浪的日子也不是这么按部就班,平平淡淡的。
我遇到过好几个有意思的人,也遇到过好几次危及生命的事。
某次我在没吃早餐的情况下,背着废品急匆匆的朝收购站的方向赶去,中途却两眼一黑,因为低血糖的缘故晕了过去。
醒来时街道上依旧人来人往,口袋里的瓶子散了一地,偶尔有路人好奇的眼光扫射过来,随后又急匆匆的赶路。
若不是因为有人不经意的瞥我一眼,恐怕我就要怀疑自己变成了透明人一样的存在。
有次我在图书馆里看叔本华的书着了迷,于是意图跑到玉案山深处的树林里,通过绝食的方式悟道,结果差点饿倒在里面出不来。
有次我走在前去吃百家饭的路上,忽然没来由的全身乏力,额头冒冷汗,腹痛如刀绞。
我像一条自知时日无多的病狗一般,举步维艰的挪回了藏身处,在睡了一觉后,居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那时我真以为自己快要寄了,于是一直在心里默念佛号,结果阿弥陀佛没见成,依旧生龙活虎的活到了现在。
后来某天夜晚,我像往常一样到碧鸡名城打宝箱,一个长相有些憨厚的小保安从身后叫住了我,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打临时工。
于是我就那样认识了小莫。
翌日清晨,我按约定来到小莫执勤的二号楼后,他用对讲机呼了个同事前来顶岗,随后带我到宿舍进行面试。
负责面试的是一位来自东北的中年男性,他是退伍军人,为人风趣健谈,我们叫他炳队。
他以为我是小莫介绍来一起打寒假工的同学,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做完入职登记后,炳队说,临时工日薪150一天包吃住,人走帐清。
没签劳动合同,或许本就是故意没弄,而当时的我工作经验浅薄,这也为之后留下了一个隐患。
我们这些临时工并非物业直招的保安,而是通过一家叫金盾的保安公司招进来的,属于第三方外包。
领完制服后,炳队把我安排到了一号楼,据说那里住了好几个物业领导,而之所以把我安排在那里,大概是因为我看起来比别人更稳重的缘故。
我还记得有个整天在小区里骑着自行车疯跑,才十三岁的小丫头,她长得有点像韩国电影《孤胆特工》里面的金赛纶。
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找我们这些临时保安唠嗑。
没成想被她给看到了,过了一会便拎着一提卷纸塞到我的岗位上,说是在路边捡到的。
我塞给她钱,她却怎么都不肯要。
由于炳队规定在岗位上不能玩手机,正巧我没有手机,于是便从藏身处拿了两本书来看。
这他倒是不反对,而另外一些同事就窝火了,每次玩手机都要偷偷摸摸的,被他发现了就是罚款警告。
当时碧鸡名城有两派保安,一派是物业直招的正式保安,他们是年纪长我们不少的大叔,主要负责诸如停车场岗亭之类的室外执勤。
而另一派就是我们这些临时工,属于室内形象岗,是第三方外包。
所有同事加起来差不多有十余人,除我之外,几乎都是来打寒假工的职校生和大学生。
当然,金盾保安公司也有正式工,他们白天会在银行或其他小区上夜班,晚上则会到碧鸡名城上夜班,睡一觉就可以领双份工资。
某次我在宿舍里睡得正香的时候,金盾上夜班的正式工忽然跑进宿舍一阵大吼大叫。
看我们被吵醒后睡眼惺忪的模样,他开心的哈哈大笑,这件事发生后,我就回到了大观楼村的藏身处休息。
而管理我们的除了炳队外,还有个金盾的主管,我不记得他姓什么了,只记得他留着莫西干发型,很擅长给我们画饼。
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宿舍给我们开例会,他的言辞很浮夸,我每次听了都会在心里暗暗发笑。
当时我们吃的工作餐,是从附近一个老式小区里做好了之后送过来的,那地方也是女生宿舍,而这个一室一厅的商铺房则被改成了男生宿舍。
有同事在例会上提议能不能把伙食改善一下的时候,主管满口答应。
因为伙食实在太过寡淡,几乎每天都是大白菜和土豆轮流炒,菜里除了一些肥肉之外,并没什么油水。
主管信誓旦旦的许诺,等过年时会给我们做一顿丰盛的大餐。
那后来直到离开时,都没看到过那个主管出现在我们面前,估计他已经心虚了。
春节过后,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学生们要离职走人,却被告知工资要到下个月25号才发放。
有人质问炳队,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人走帐清的吗?
结果对方却翻脸不认,压根不承认自己有说过这些话,这下空口无凭,大家都吃了没签合同的亏。
我找炳队理论,说了一套大家出来打工都不容易的委婉说辞,没成想把对方给惹恼了,直接冲我叫嚣,不服你们可以报妖妖零,可以去劳动局告。
现场有个女生已经急得哭出了声,她来这里打工只是为了挣学费,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实在没料到会是这种局面,平时亲和健谈的炳队在此刻忽然翻脸,跟变了个人似的。
有同事小声商量着要不要通过爬到楼顶威胁的方式来讨工资,大家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
我向小莫借了手机后拨通了主管的号码,把大家的诉求向他描述了一番后,主管承诺会预支部分工资给我们。
于是我便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发给了他,并把这件事告知了大家,随后在炳队的命令下,我们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
下午的时候,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千块的预支工资,当时我们已经在那里做了四十来天。
当天晚上,我便离开了这个地方,而至于剩下的五千多块工资,我至今都没有收到。
后来,昆明第N次创建文明城市,街上的流浪汉也随之减少,他们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存活着。
过完冬后,天气逐渐暖和起来,西伯利亚海鸥陆续从昆明飞走,飞向它们起始的出发地。
而我也在那时离开了昆明,朝着那个工业遍地,莺飞草长的江南走去。